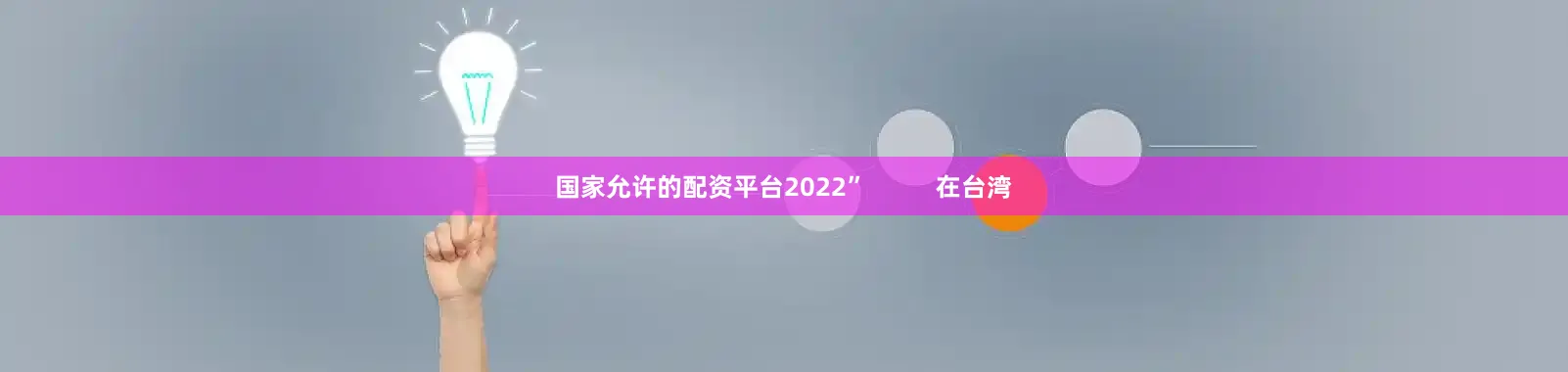
2005年9月20日晨,北京天安门城楼的风掠过七旬老人深蓝色的风衣。李敖拄着拐杖,目光扫过黄缎锦垫的扶手椅——那是1949年毛泽东宣告新中国诞生的历史坐标。讲解员邀他落座时,他竟后退半步,低声笑道:“这椅子会烧屁股。”一句戏言,裹着沉甸甸的敬畏。
当记者簇拥着请他向广场挥手,他手臂抬至半空忽又垂落:“这地方不能乱挥手,挥手有分量,我担不起。” 人群倏然静默,快门声戛然而止。

临行前,他提笔在留言簿写下“休戚与共”。墨迹未干,解释已至:“休是喜,戚是忧,共是共产党。大陆好,我同喜;大陆难,我同忧。” 四个字如一把钥匙,开启了他漂泊五十六年的赤子心锁。
根脉:松花江畔到台北牢狱的淬炼
1935年哈尔滨的寒冬,日军装甲车碾过冰冻的松花江。六岁的李敖蜷缩家中,摩挲着父亲李邦彦珍藏的油印《新青年》。母亲告诉他:“马列”二字是“穷人翻身的指望”。父亲表面调度铁路货运,实为中共地下交通员,夜色中传递的情报织成他童年的底色。
1945年北平胡同里,少年将一枚铜圆放入八路军伤兵掌心。对方颤巍巍的军礼烙进他记忆:“那是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国家。” 四年后风云突变,十四岁的他随父赴台,船过澎湖海峡时,他紧盯北斗星在日记立誓:“总得回来。”

在台湾,他成了“反蒋斗士”。《孙中山研究》《蒋介石传》如利剑出鞘,九十六本著作遭查禁,三陷囹圄。铁窗岁月里,他竟抄写《毛选》度日。同囚不解,他答:“读给自己壮胆。” 牢狱未能驯服狂骨,反淬炼出更锐利的家国锋芒。
真章:七个诘问剖开历史迷雾
“唯毛主席值得我喊万岁,他人不配!” 此言非一时兴起。2005年北大讲台上,他擎着《毛泽东文集》质问学生:“很多人说共产党不让说话,可‘犯了错误就要承认’这话你们读了吗?”掌声雷动中他挑眉:“看书别光听人讲!”

面对质疑毛泽东的声浪,他掷出七问:
“若置身井冈山烽火,你能否推翻三座大山? 面对国民党围剿,可带红军穿越雪山草地? 四渡赤水时,能否将数倍蒋军玩弄股掌? 抗美援朝时,可击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?”
每一问皆刺破浮议。他深知毛泽东的争议,却更重其立国之功:“蒋介石的错导致失败,毛泽东的错发生在成功之后。” 在清华演讲时,他再以六个“有本事”反诘否定历史者:“有本事就把两弹一星拆掉重造!有本事就让联合国军再打到鸭绿江!” 锋芒所向,俱是守护民族精神的铠甲。
余响:十四箱手稿与一句遗嘱
天安门之行后,“休戚与共”在岛内掀起轩然大波。绿媒讥其“自我矮化”,他肃然回应:“城楼是中国新纪元的起点,我敬的是历史!” 演讲散场时,他总向前排学子深鞠一躬:“你们是未来的中国,我对未来行礼。”

此非一时感怀。2010年携妻儿重游大陆时,他凝视西湖烟波对儿子李戡说:“台湾终将统一,这是常识。” 八年后病榻弥留,他指着手稿箱交代:“《毛泽东文集》留给李戡,将来你要知道谁是真正的中国人。” 十四箱思想遗产中,这句附注成了穿越生死的家训。
更意味深长的是文化赎还。他曾讥北京故宫“真品不多”,2007年却亲携乾隆御批书画跋语捐赠,坦然认错:“真正的故宫在北京。” 从批判到敬重,恰似他的人生隐喻——了解愈深,偏见愈消。

##
2011年厦门大学讲台上,七十六岁的李敖望向黑压压的年轻面孔。那些举起《毛选》的手,那些天安门下“大学长”的呼喊,已汇成他晚年的星图。登机离京那日,他回望逐渐缩小的华北平原,耳边响起五十六年前离乡时火车的嘶鸣。当年窗外焦土,而今山河重光。
狂士终其一生以笔为刀,却在毛泽东的画像前垂手肃立。那三个天安门上的动作——拒坐、收手、题字——如楔入历史的铆钉,将漂泊者的灵魂铆在故土。
国内股票配资,云南炒股配资公司,炒股配资开户识必选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